金融科技促进消费:从经济学逻辑到现实路径

导语
包括电子消费券、电子钱包在内的金融科技能够缓解消费者在储蓄、投资和消费之间转换的约束,通过使消费回暖,撬动经济复苏。
近年来,消费已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然而,新冠肺炎疫情使得消费市场受到较大冲击,诸如餐饮、购物、酒店住宿、文化娱乐、旅游休闲等消费活动出现不同程度萎缩。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0年1—2月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20.5%,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28.7个百分点。疫情对居民消费的不利影响,削弱了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的作用,并对经济运行形成拖累。如何促进消费,提振经济活力是各方关注的重中之重。
电子消费券:应对“高储蓄率”的有效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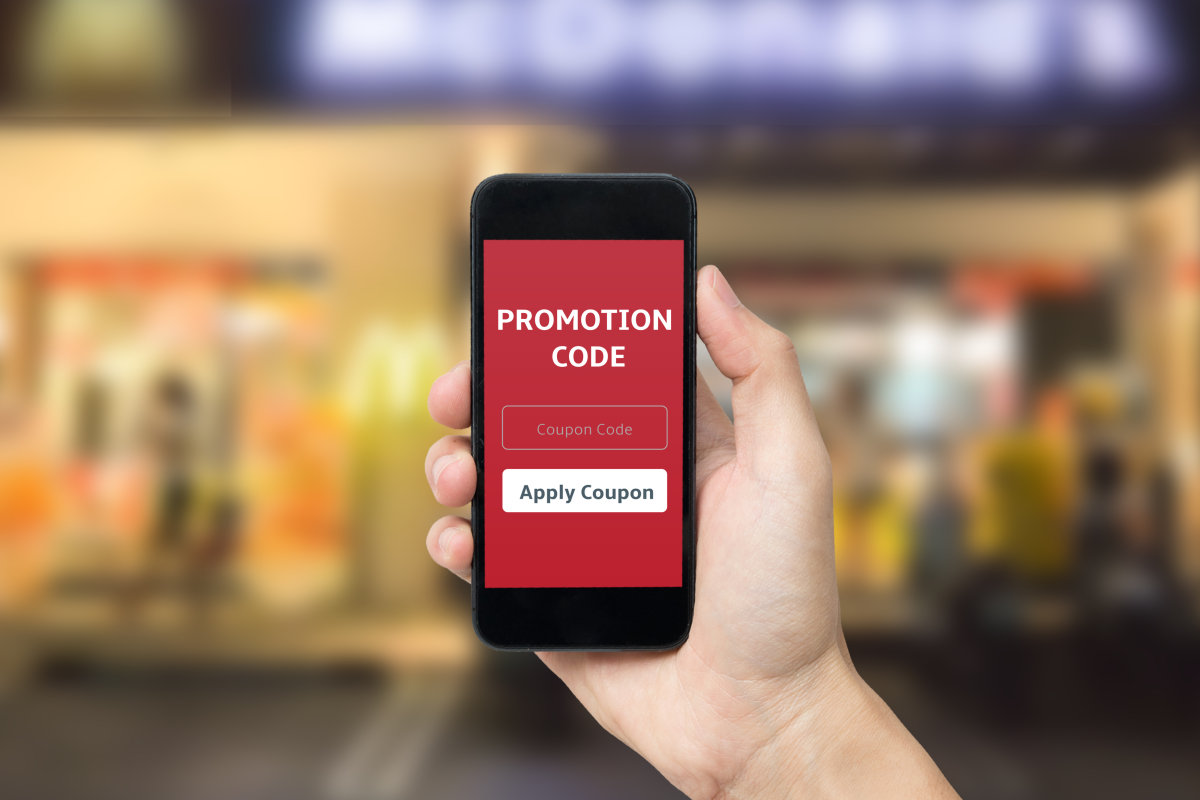
消费问题的背后,其实是复杂的经济链条。消费需要支付货币,无论这个货币的形式是什么。这笔钱从消费者到商家手中,商家才有钱支付上游进货款项和员工工资。整个经济链条才能运转起来。因此,在经济发展陷入停顿的情况下,很多政府选择的是以工代赈。即使一定要发放赈资,也避免直接赈实物,而是尽量在消费环节注入货币等支付手段,并且注意避免转为储蓄,让人们完成消费的同时,推动资金流转、交易发生、生产复苏和经济回暖。
这个支付手段应该是现金,还是消费券?应该是电子券,还是纸质券?一时间引发了不少讨论。现金应该是最后的选择。首先是因为现金的发放容易引发通胀。如果这些现金来自财政转移支付,那么尚且可以说是“按需分配”。如果这些现金来自印钞机,那么通胀以及带来的物价飞涨,很快会让发放现金失去意义——本来买不起的东西,还是买不起。而且,货币超发会导致不同资产价格膨胀的程度不同,以国人买房保值的习惯,这笔钱很可能还是会流到楼市。
其次是很难确保现金能够用于消费。理论上说,收入越低,边际消费倾向(MPC)递增。但是,Francesco D'Acunto和Thomas Rauter等人最近在NBER发表的工作论文《预防性储蓄的动机:来自金融科技的证据》发现,当穷人缺乏社会保障时,获得一笔额外收入,他们是不会消费的,而是会作为预防性储蓄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1]。从NBER的这篇文章,我们或许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现金对于穷人可能不完全是“支付工具”,而是一种预防性储蓄——无论是存进银行,还是藏在枕头下面。
所以,以什么形式补贴引导人们用这笔补贴去消费呢?消费券[2]对促进消费有没有用呢?从境外的经验看,很可能是有用的[3]。研究发现,“2009年台湾地区购物券计划”对边际消费倾向的促进效果约为24%,即1新台币消费券的使用产生了0.24新台币的计划外消费,扣除商家促销后,仍有16.4%[4]。不过,我国台湾地区的消费券也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无法记名、无法跟踪,难以统计其真实激励效果,加之存在转让、套现的“空子”,使得消费券最终未能达到预期的激励效果。
研究者指出,看消费券对于提振边际消费倾向的促进效果(美国是30%~35%),不能不考虑储蓄率和消费心理。以2012年的数据看,我国台湾地区个人储蓄率为21.21%,日本为19%,而美国仅为7.2%。考虑到台湾地区的消费券可以在二级市场进行交易,不排除有市民领到消费券后进行了转让,形成现金后转为储蓄。甚至有人低价卖给商户,或“先以券买,再退货”,套出现金。整体看来,由于消费券是纸质发放,领用之后如何使用,如何流转,促进了哪些人群的哪些商品消费,是笔糊涂账。由此看来,电子消费券可能是更优的选择[5]。
电子消费券的好处是避免出现冒领、转卖、炒券等行为,且消费券能够在支付环节直接使用回收,便于统计兑付;少量专享现金的好处是,能够让困难群众解燃眉之急。二者结合,可能是最为合适的安排。无论是发放纸质消费券、现金还是电子消费券,本质上都是为了让消费迅速“回血”。有人问,为什么国外政府只能直接发钱,而中国政府可以发消费券?因为,中国在数字经济的发展方面走在前面。具体来说有以下三点。
一是终端的普及度够高,两家支付平台几乎覆盖了大部分消费人口;而且各类本地生活平台,通过移动支付接入的消费场景也够多够广;消费券作为电子支付工具,完全可以在支付环节就直接发挥作用。
二是电子消费券不是直接给钱,而是给消费折扣,它对于有消费需求的人群精准补贴;对于那些没有补贴需求、不打算消费的人,这些券就是废纸,政府也可以减少投入;政府发出10亿、20亿元的消费券,最终真正兑付的额度肯定低于此。
三是电子消费券实际是大数据治理的一种尝试。它能够精确地将消费券给到居住在当地的人群,也能够在商家端圈出一批真正受消费者欢迎、放心消费的好商家。在一轮轮发放中,也可以根据领取率、使用率实时再作调整;如果是纸质券或现金,这种实时统计和调整都将非常困难。
总之,身处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开端,中国在数字经济的发展中也确实有微弱的领先优势,这为我们使用电子消费券而非纸质券或现金提供了技术保障和用户基础。如果因为实际并没有那么严重的数字鸿沟,就要往回走,回到纸质券或现金赈灾的年代,那么这些年积累下的数字经济微弱优势恐怕就白白浪费了,而且,可能还会错失政务数字化加速转型的良机。
电子钱包的延伸形态:消费信贷与余额理财

正如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是全局性的,消费带来的经济改善意义可能是系统性的。当前,疫情在国内整体可控,但在世界范围内蔓延。大量出口型企业,或是因为客户也陷入疫情困难,或是因出口途径受阻,继复工难、用工荒、资金紧之后,遇到了订单断流的致命一击。在此背景下,处处可见的是一种不敢花钱、不愿花钱的心态。内需存在后继不足的问题,很可能会加剧生产停滞、工厂停工的恶性循环。
这个时候,需要两种流动性提供机制。一种是前面讲到的“公共救济”,即消费券;另一种是更市场化的消费信贷。疫情暴发的当下,消费信贷的应用,一方面会使人们敢花钱,在该吃该用该治疗该置办的时候有助力。另一方面,会为商家提供流动性,消费者花了钱,商家、企业才能活下去,在企业工作的人们才能活下去。
前面提到的《预防性储蓄的动机:来自金融科技的证据》一文中提到,当穷人缺乏社会保障时,即使获得一笔额外收入,也是不会消费的,而是会作为预防性储蓄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倘若用户获得了消费信贷额度,他们反而会减少预防性储蓄,更敢花钱。计算发现,那些获得消费信贷额度的用户平均增加了相当于收入流水的4.5%的消费。而且,几乎所有用户(90%)都会优先使用流动资金,这就减少了“恶性债务”,因为他们不会利用透支额度。换句话说,大部分人通过消费信贷额度获得的是一种安全感,一种敢于少存钱、少留现金在身边的“保险”。
这样的消费信贷,一方面本身就是普惠金融的重要部分,让那些收入较低的人群得以解燃眉之急;另一方面,实际上也是基于人们还款能力设计的周期性平滑工具。这并非寅吃卯粮,而是让确有未来收入能力的人们降低储蓄压力,不要等到冬天才有钱买空调,等夏天才有钱买棉袄。不过,要怎样确保那些钱能精准地用在消费,而不是流向股市或房市呢?场景就特别重要。和现金贷不同,互联网消费信贷大多与场景密不可分,它甚至就植入线上、线下消费的支付场景,让人们在消费时多一个分期的选择,同时确保这笔信贷真的能打到场景里提供了商品或服务的商家手中。
无论是线上消费、还是线下支付,消费信贷为了确保“钱用到刀刃上”,都要求有着明晰的消费场景。贷款方能够通过场景,确保这笔信贷确实用在了消费上。同时,能够通过场景积累使用者和商户的信用,进而降低信贷违约的可能性。最近涌现的问题是,如何识别串通套现,防止出现“代刷”问题。这可能需要对商家的信用体系进行建库和评估。那些具备较好商业信用的商家,可以接入更多的消费信贷支付工具,形成与商家绑定的消费信贷业务;同理,对于消费者,信用较好的消费者,押金、保证金也可以暂不提交,省下流动资金和信用额度。
从长远来看,有时金融科技的发展还能够打通一些看似不相关的领域,给小商家和消费者以微小的红利。以前,小卖部每天收摊后要算账、盘点、对货,然后锁上门,小心翼翼地捧着零钱箱,赶在银行关门前存掉今天的利润。可能收到假钞,到了银行才发现;路上捧着零钱,要提防小偷小摸。这些不说,即使到了银行排半天队,也只能存活期,几乎没有利息。而如果能通过二维码收款,钱直接进入理财工具。小商贩不用留出一笔零钱来找零,消费者也不用携带零钱,让每一分钱都实时得以获得理财收益,即所谓的“双边市场效应”(two sides market effect),让消费环节获得来自资本市场的红利。
打通理财与消费支付,让货币市场基金变成支付工具,这从资金流转上有赖于微信、支付宝等平台的“T+0”资金实时划转。实际上,通过零钱理财平台的资金,要等到第二个工作日才由基金公司进行份额确认(即所谓“T+1”),对已确认的份额会开始计算收益。而发生赎回时,实质是货币基金的卖出,这也要到第二个工作日资金才能返回投资者账户。移动理财平台之所以能做到“T+0”,实际上是以巨量沉淀资金做后盾,倚赖庞大却分散的客户群,以先行垫付的方式实现。而从内核看,在海量存入取出的瞬间并发计算需求,以及对于流动性安全状况的压力监测,都需要平台有极强的“大脑”:云计算与人工智能——这才是余额理财能够用于作为支付工具的秘密所在。
然而此举的益处也很明显。传统金融市场下消费者在储蓄、投资和消费之间转换的约束大大缓解,消费者可以在既定的总收入水平下,极为便利地将储蓄用于投资,随时可以将储蓄和投资收益转化为消费支出,有利于改善消费条件,提高消费倾向。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数据分析,移动支付可促进中国家庭消费16.01%的增长。此外,为电商和支付平台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降低了线下交易成本,带来了双市场的消费便利。如前所说,店家使用移动支付收款,钱立即从余额进入理财。而消费者与商家会在支付选择上互相影响,不能扫码支付的商家会迫于压力,抓紧转型——从而在两个市场都形成理财红利的反哺,促进消费的同时让扫码消费成为国人最习惯的支付方式。
总之,我们希望看到,人们在进行消费时,能有一个信贷支付的选项,用借来的钱撬动经济复苏;希望看到人们利用消费券在特定场景中进行消费,兑现那些精准投放的补贴;希望小商家再也不用捧着零钱走战战兢兢的夜路,能轻松在手机上进行货、客、账的盘点。
J.F.肯尼迪曾说,在汉语中,危机两个汉字,拆开就意味着危险与机会。这次疫情既是全民之危,又是一次改变行业轨迹和赈灾方式的契机,是一次推动消费与金融转型的契机。希望借力金融科技,能够通过使消费回暖,让经济复苏,甚至超越往昔。
注释:
[1] Francesco D'Acunto,Thomas Rauter,Christoph Scheuch,Michael Weber. “Precautionary Savings Motives: Evidence from FinTech.” https://www.nber.org/papers/w26817。
[2] 历史上第一个食品券计划早在1939年在美国诞生。这个计划的名称是“补充营养援助项目”(SNAP),政府向低收入者免费发放食品券,低收入者凭券到符合条件的零售店购买食品,然后政府用现金兑现各个零售店收到的食品券。食品券分为1美元、5美元和10美元,只能在特定场所(一般限于面包店和超市等)购买指定食物(如果蔬食品),但不能在餐馆消费,不得购买垃圾食品、碳酸饮料和烟酒等。
[3] 以日本为例,1999年向15 岁以下儿童、65 岁以上老人以及领取福利养老金的老人每人发放2万日元名为“地域振兴券”的购物券,总额达6000多亿日元,用于鼓励居民增加生活消费。根据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Chang-Tai Hsieh等人的研究(Did Japan's shopping coupon program increase spending?),用1999年与1990—1998年的家庭消费支出数据作对比研究,结果表明:消费券增加边际消费倾向20%~30%。消费券对整体居民家庭消费有明显的提振作用,阶段性地扭转了居民消费持续下行的趋势。1999年日本GDP家庭消费同比增速从1998年的-0.8%扭转至1%。一般家庭获得的优惠券价值为家庭月收入的7%~8%,消费券对于居民消费支出额外提高10%。尽管2000年,伴随消费券发放的结束,居民消费增速亦有所回落,但始终没有跌破消费券发放前增速的低点。这说明消费券没有提前透支消费需求,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刺激需求的回暖。
[4] Kamhon Kan, Shin-kun Peng, and Ping Wang,Understanding Consumption Behavior: Evidence from Consumers’ Reaction to Shopping Vouchers.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 2017,9 (1):137-153. .
[5] 当下有一些因为极少数困难群众无法使用消费券、从而呼吁全民发放现金的声音,并称其为“数字鸿沟”。值得说明的是,数字鸿沟问题可能被夸大了。据报道,杭州发放价值4.85亿元电子消费券的同时,专门准备了1 500万元现金的困难群众专享现金。所谓困难群众,可能指的是没有智能手机,或是学不会使用智能手机、身边又无能够代劳的亲友的群体。他们无法领取消费券。因此,民政部门为其准备了1 500万元的专享现金。
*本文经原作者授权,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