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栖经济学家的身份图谱——对话邵宇

导语
跳出数理模型的单一框架,以动态视角融合人文关怀于现代经济金融研究。

从语言学专业跨界到金融,并建树颇丰的邵宇博士,追溯他在复旦大学学习与生活的点滴。以专业的角度与独特的思考,他分享了自己跳出数理模型的单一框架,以动态视角融合人文关怀于现代经济金融研究的经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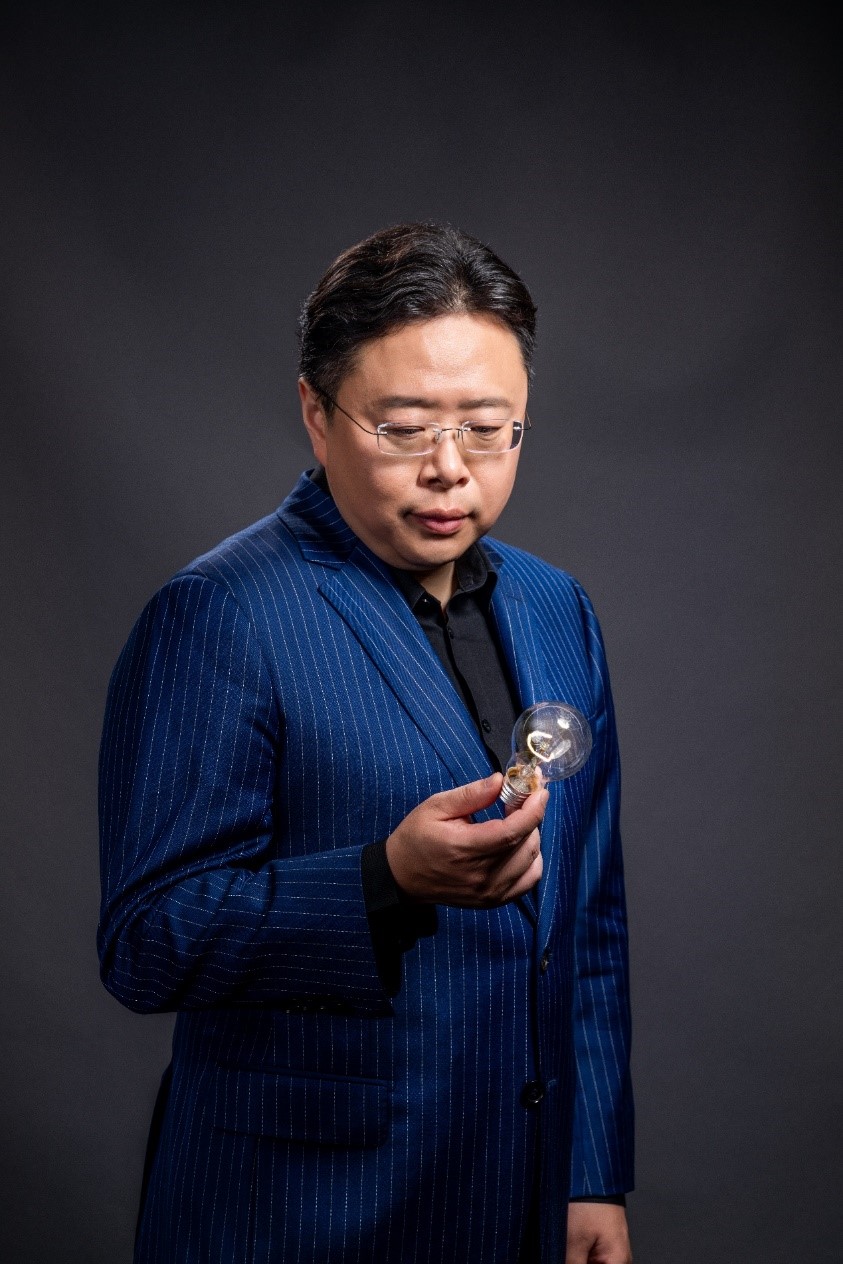
通识教育影响思维模式
高华声:邵博士,当初您为何从语言学跨界到金融,而且能够如此成功?
邵宇:当时我学的是中文专业,主要是读文学作品,看小说诗歌,你也许会纳闷这对经济研究有什么帮助?在我看来,语言和人文学科会给你一种基本的训练和熏陶。相比理工背景或纯经济学背景的专家同行,在这种影响下我写的文章可能更具人文关照和历史视角,以及政治等各方面因素的考虑。曾经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认为经济学不外乎统计、计量、数理模型的推导。其实,经济学是一个十分注重人文的学科。谈到经济危机、金融市场的起伏往往涉及过往历史,关联到后人会不会重复某段历史。对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思考以及人文的关怀,会渗透到个人的研究和写作中。人文领域的熏陶可以拓宽认知的角度,帮助我们从更深的层次理解经济和金融现象,做出更为合理的判断。
高华声:的确。不少中国乃至世界著名的金融学家、经济学家都是从人文学科出发的,比如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金融学教授尤金·法玛(Eugene F. Fama)是主修法文出身。
早年的经历扩大了您的思想广度和深度,跳出数理模型的单一框架,使您得以将人文关怀融入现代经济和金融体系,这其实是一种非常稀缺的经历提升。接着这个话题想请教您,如今的新生代学生所接受的训练和您求学时候有何不同?对当代学生的培养,我们可以重点关注哪些方面?
邵宇:在教学相长的过程中,我注意到现在的年轻一代学生的感知更为敏锐,学科基础更扎实,不管是读MBA、EMBA,还是金融博士专业,都是“武装到牙齿”。从技术层面说,相对同时期的我们,现在的学生接受的训练更为完整。但我总觉得他们身上缺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很大程度上还是对整个社会的关怀,也就是人文关怀。这可能是学生在课堂上、在与老师的交流中、在校园气氛的熏陶下收获于无形。
我在英国牛津大学做过一年访问学者,其间也在做我的博士后研究。当时牛津大学有一家商学院叫萨伊德商学院,我很少去拜访,反而花了很多时间参访神学院、政治学院、人文学院这些与我专业看似无关的院系,与那里的老师和同学进行交流切磋。事后想起来,那段经历对我启发非常大。回望这些感悟较深的历程和实践,我建议同学们全面地开阔眼界,不要仅仅局限于眼前的一个模型、一个回归分析或一个商业案例的分享;打开你的眼界,充分利用复旦的资源和社会其他资源,对提高整体素质是非常有帮助的。
深耕中历练,动态中实践
高华声:此前,您曾公开表达了对现今的金融学教育的一些不满,调侃现在的金融学毕业生“上不能预测宏观经济,下不能建模做公司估值”。我对这两句话印象深刻,借此替广大金融学子向您请教:宏观经济分析、建模与公司估值等能力,应该在求学阶段掌握好,还是在未来的金融生涯习得?学金融的过程中,哪方面能力更重要?
邵宇:我自身的经历贯穿教学互动的整个过程,回想我在硕士及博士阶段学到的东西,大部分是金融学的经典模型和研究方法。其实,当今主要院校传授的内容基本还是这些,培养出来的学生难免为条条框框为束缚。但实际上金融和经济是非常动态的学科。曾经我们一度认为理论研究已经走到尽头了,再深究下去都是些细枝末节的问题,而事实正好相反。从2008年金融危机到现在,传统的经济学,不管是宏观还是微观方向的很多理论框架都在经历一个被动摇的过程。
从我自身经历来说,我博士毕业以后在复旦任教将近八年,2008年离开学校进入实践领域,很大原因在于我发现做了这么多年老师,教给同学的东西大部分都过时了,甚至绝大部分是错误的,如此下去不是误人子弟吗?因此,我选择投身市场做一些实践工作。十年之后的今天回顾这个转身,对它的理解比当时更为全面。纯粹用理论刻画的东西能够体现的只是一种基础的方法论,经过十余年微观和宏观领域的实践研究,我才得以全面拓展早年在学校学到的那些最基本的框架。
高华声:在复旦求学及授课期间,对自己影响最深远的人是谁?
邵宇: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的博士生导师,陈观烈教授。陈老师主要研究国际金融,带了我一年博士生研究后便去世了。从师于他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他的学术风格、研究的领域给我带来特别深刻的影响。我记得当时他研究的是美元霸权,包括美元如何影响全球经济的变化、全球化体系如何塑造,我之后写了很多关于全球化的书,包括《全球化4.0》《危机三部曲》,某种意义上可能是陈老师的学术框架在我身上的一种折射和延伸。
更重要的是,陈老师为人和做学问力求严谨。他出版的著作非常少,相比出书他更看重自己的教学和研究,如果作品没有非常成熟,他不会拿出来,在这一点上我自己也觉得比较惭愧,我现在大概一年出一本书。其实,真正的创新是非常稀缺、有限的,因此才需要花更多精力去做。这就意味着我要做更多对自己研究的打磨,这样呈现出来的内容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对自己、对学生、对社会是一种更负责任的做法。

身份切换,游刃有余
高华声:您现在的身份之一是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首席经济学家在券商行业具体从事什么工作?作为一位复旦大学的毕业生,如果以后想跟随您的职业发展路径,在某些著名券商或知名机构成为首席经济学家,他们需要做哪些准备?
邵宇:我认为做经济理论的研究者大致有三类:第一类就是像您一样在学校做理论或偏理论方面的研究,主要工作是发论文,力求在学术圈得到认可。对于他们来说,理论基础无疑是第一位的。
第二类是政策型的经济学家,比如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或中国社科院,他们主要工作是做政策研究,如在金融危机或疫情以后经济会如何发展。他们主要从事政策类的研究和建议。
第三类是市场经济学家,我也是其中之一。我们主要研究市场动态,受众主要是投资人和投资机构。这一类市场经济学家通常被券商、投行聘用,当然也有商业银行,其中大多数是被投行聘用,我们称之为“卖方的经济学家”,主要为投资人提供观点和投资建议。这类经济学家较前两类更为活跃,他们在媒体和市场中对应不同的身份。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经济学家需要能够在这三类身份之间自由转换,一是有能力建立理论的模型,二是有能力提供优质的政策,三是也能为投资人提供明确的投资判断。
其实,同时承担这三个领域的工作是不容易的,但是很有意义。比如我们有首席经济学家论坛,首席经济学家们给决策者提供来自市场领域的投资决策或观点。市场经济学家原先基于商业判断做的一个研究,如果也能为决策者提供政策性指导,那么这个研究就具备更大的社会效益。
经济学家如果能够不断地在学界、政界或政策研究领域以及商业界来回流动,不仅能催生更好的研究成果、理论模型和系列书籍,而且能够在这三者之间产生一个自由交流和转换身份的空间,慢慢就会成为另一种复合型的职业发展趋势。
高华声:感谢邵博士的精彩分享!您在复旦求学、任教期间的各种经历告诉我们,除了加强自己的理论修为和专业技能,也要抓住时机,充分利用复旦大学文理兼修的特点,加深自己的人文修养,通过文史哲触类旁通,这将对我们的职业发展有长久的好处。
*本文经原作者授权,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