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支持“新就业形态”释放潜力?

导语
新就业形态以就业领域新、技术手段新、组织方式新、就业观念新的特点,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在就业优先战略下,应以更大力度支持新就业形态释放巨大潜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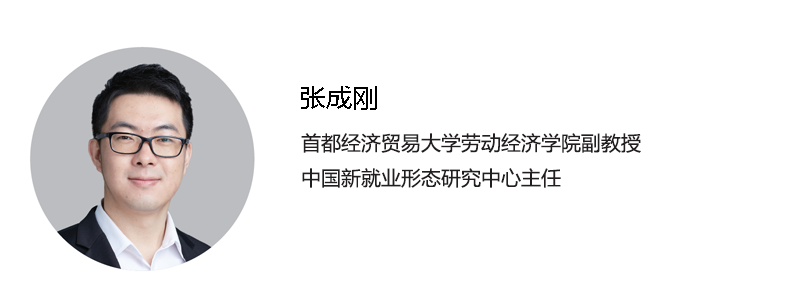
世界范围内,劳动力市场正在经历着新就业形态的出现和扩散。新就业形态是一种新兴的就业模式,其中劳动者通过网络平台找到工作和任务,而不是通过传统的雇佣方式获得工作和任务。这种新型的就业模式正在改变劳动力市场的雇佣模式,并对全球劳动力市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政策制定者、学术界、企业界和劳动者应该对这一劳动力市场新现象有更加明确的认知,以适应和应对这一趋势性现象的影响。
界说“新就业形态”

图源:VEER
对新就业形态的概念一直颇有争议。第一个争议是新就业形态新在何处。笔者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概括了新就业形态的“四新”(张成刚,2016):一是就业领域新。新就业形态大量出现在小微创业企业、电子商务、分享经济、社群经济等新经济、新业态中。二是技术手段新。新就业形态依托互联网、大数据、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极大地降低了就业服务的交易成本,提高了劳动者与企业、消费者的匹配效率,实现劳动供需快速对接,扩大了就业服务的时间和空间范围。三是组织方式新。新就业形态下劳动者与组织的关系更松散、灵活,许多劳动者个体不再作为“单位人”来就业,而是通过信息技术、各类平台或是与市场细分领域的连接,实现个人与工作机会的对接,去组织化特征明显。四是就业观念新。许多就业者不再追求“铁饭碗”式稳定的就业,而更愿意从事灵活性与自主程度高的工作。就业者对自我价值创造与兴趣爱好实现有更强的诉求,对组织的依赖感下降。对新就业形态“四新”的概括被很多文献引用,但今天看来这一概括更多是在现象层面的描述。
新就业形态的“新”本质上是以数字技术构建的平台系统为核心,对劳动力要素进行组织和调配,从而实现劳动者与劳动需求在一定空间范围内匹配的市场体系和合约模式。在该市场体系下,平台企业撮合劳动者(被称为独立承包商、自由职业者)与消费者形成合约关系,平台企业不与劳动者签订全职雇佣合同。因此,数字技术是新就业形态的技术基础,数字平台系统是新就业形态的组织基础。新就业形态构建中尚缺乏社会基础,包括制度基础、社会共识基础等,这需要更长时间的构建。总体而言,发达国家的劳动法律更为健全,因而形成新的、适应新就业形态的制度规范阻力更大。这是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的一个差异。此外,中国劳动力市场中规模庞大的灵活就业者为新就业形态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要素基础,这是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的另一个差异。
这里需要强调新就业形态的组织基础,即新就业形态的发展离不开平台企业搭建的平台。平台企业搭建了技术和应用的双层结构(姜奇平,2017),平台属于基于技术的应用层面,是平台企业依托数字技术,并通过服务协议条款确定交易规则和标准以实现控制和协调的基础设施。平台企业通过平台组织方式能够扩大规模,发挥平台的网络效应。以上描述意在表明,平台企业与平台不是一回事。平台是受平台企业、交易多方和政府规制等力量影响形成的自由市场体系,最终目的服务于让独立工作者与服务的购买者高效率地完成交易。由于平台属于双边或多边市场[1](Evans and Gawer,2016),平台网络效应既可以放大平台价值,也可以放大平台缺陷,因此平台运营成本和对运营能力的要求相对传统企业更高。
第二个争议是对新就业形态相关现象缺乏明确、统一的概念,这对于全社会理解新就业形态造成了困难。研究文献中与新就业形态密切相关的术语众多,如共享经济(Sharing Economy)、应需经济(On-demandEconomy)、应需工作(On-demand Job)、优步经济(Uber-economy)、优步化的工作(Ubernization)、零工经济(Gig Economy)、零工工人(Gig Worker)、平台经济(Platform Economy)、协同经济(Collaborative Economy)。国内学者也发明了一些术语来描述新就业形态现象,如P2P 用工模式(点对点用工)、互联网App平台用工、下载劳动等。使用何种术语来概括新就业形态这种现象基本上没有高下的区别,只要是学术界和社会对此术语有共同的认可,对术语反映的内涵有共同的认知即可。学术界其实不需要发明太多术语来讨论同一现象。例如,有学者不使用学术界广为流行的“零工”这一更广泛的说法,而发明了“灵工”的术语[2],这样的概念创造并未增加我们对现象的认知,反而会进一步加剧概念的混乱。
作为较早从事新就业形态研究的研究者,笔者在大多数情况下选择新就业形态这一术语的原因在于,“新就业形态”作为《政府工作报告》和政策文件中多次出现的术语,相对而言有最广大的覆盖范围和阅读范围,更容易在社会各界形成共识,也更容易在政策层面形成沟通。
第三个争议是关于新就业形态和灵活就业的关系问题,既是社会各界纠结的问题,也是很多传统思路抵制新就业形态的保留地。在搞清楚新就业形态和灵活就业的关系问题前,首先应该了解灵活就业的概念内涵。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1年国有企业改革“下岗潮”期间,有大批国有企业劳动者在短时间内丧失体制内的劳动收入来源,涌向当时发展并不完善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界引入国际劳工组织的“非正规就业”概念来描述这一群体。在上海市解决下岗职工再就业工作中,引入非正规就业概念(柏宁湘和郑永新,1997;欣达,1997),但后来出于积极修辞的考虑,将非正规就业的说法修改为
灵活就业,以后的政策文件都使用灵活就业这一术语[3]。
因此,在国有企业改革“下岗潮”的语境下,灵活就业和非正规就业是描述同一现象的两个术语。2000年左右,主流媒体仍然使用非正规就业这一术语,如陈淮(2000)将非正规就业定义为:“非正规就业与社会保障体系之间几乎没有制度性联系或者虽有制度性规定但很少被遵守;基本报酬形式一般采取计时工资(如按天、按小时等),少数情况下采取计件工资(如零星劳务承包、产品推销等);劳动报酬一般只能达到当地法定最低工资水平;与雇主之间的劳动契约十分松散,一般处于随时可能被中止的状态;劳务收入处于税务监管的‘盲区’很少被申报纳税。”并且认为上海确立小时用工模式,实际上是正式承认了非正规就业(晓白,2001)。
新就业形态与灵活就业的联系是都不在现行劳动法律覆盖范围内,即劳动者和用工方或用工组织方无劳动关系。以没有劳动关系这个单一的维度,可以将新就业形态归到灵活就业的范畴内。但这一联系会使很多人自然地构建起一个逻辑三段论,将灵活就业特征和属性移植到新就业形态中——新就业形态属于灵活就业,灵活就业的就业质量低,所以新就业形态的就业质量低。如果抛开无劳动关系这一灵活就业与新就业形态的交集,二者在经济基础(如组织模式、技术手段、合作关系)和现实表现(如生产率水平、收入水平)等方面都存在差异。即使把新就业形态与灵活就业理解为包含的关系,那么在数字经济时代灵活就业的内涵也已经发生变化(张成刚和祝慧琳,2017)。因此,应该从更复杂的维度,或者从更新的内涵角度看待新就业形态,劳动关系角度仅仅是全貌中的一个方面,并且其内涵也应该随着就业形态的发展而发生改变,遗憾的是太多人被这个单一的概念框架困住了。
第四个争议是新就业形态的规模到底有多大。对于新就业形态规模的估计涉及对其重要性和影响的判断,也涉及政策出台的力度。要评估新就业形态的规模,需要形成对新就业形态的统计定义。非正规就业的统计定义从1973 年国际劳工组织“肯尼亚”报告首次提出非正规就业部门概念到1993年国际劳工统计大会“非正规部门就业统计决议”首次提出了非正规就业定义,再到2003年国际劳工统计大会修订非正规就业统计定义,用了30年才将一个概念的统计定义基本确定下来。因此,尽管新就业形态规模尚没有明确的官方统计,但对新就业形态已经成为劳动力市场重要现象这一事实无须赘言。即使没有官方数据,我们也不应该对“房间里的大象”紧闭双眼,应该继续加强对新就业形态的研究。目前,我国统计部门已经着手对新就业形态的统计工作做出安排。
新就业形态成为塑造劳动力市场新力量

图源:VEER
新就业形态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还未完全显现,但一些已经出现的现象值得关注。
第一,新就业形态改变了劳动力的就业方式。劳动者可以通过网络平台与服务使用者联系,直接获得工作任务,而不是通过传统的雇佣方式。这种新型的就业方式对传统的就业模式产生了挑战。当劳动者发现新就业形态能够带来更大效用,会自发做出选择。劳动力市场会回答一个新的就业模式是否适合劳动者。任何通过行政力量干预以遏制新就业形态发展的思路和观点都严重低估了这一趋势性的力量。
第二,新就业形态改变了劳动力的收入来源。新就业形态使得劳动力可以通过更分散的任务获得收入,而不是仅依靠一份固定的工作。这种收入来源的改变,对于劳动者在市场议价能力的改变会产生正向还是负向的影响,还需要更多实证研究予以回答,因为要考虑的因素太多了,包括劳动者自身所处的劳动力市场环境(如拥挤程度、进入门槛、技能要求等)、劳动者所处行业的发展水平(如市场需求程度、行业的成熟度等)。
所以,我们预测一种可能会存在的分化。那些更善于利用市场力量或对市场有更多理解的劳动者将被从单一雇主那里解放出来,形成威廉·鲍莫尔(2018)提到的创新劳动者群体;那些不善于与市场对接的劳动者将依然留在单一雇主那里。这一分化在我们过去几年的研究中有所体现,如尽管有不少专家惊呼“年轻人都去送外卖了,谁还要进工厂”,但研究发现,留在外卖平台的年轻人和进工厂的年轻人是符合不同素质模型的两批人。换句话说,从事分散地点多任务并直接面对客户的劳动者和集中于单一地点单一工作的劳动者是偏好和技能特征不同的两类劳动者。会有年轻人不断涌入新就业形态,但经过筛选最终还是只有少部分能够满足要求。
第三,新就业形态改变了劳动者的工作地点和工作时间。在线平台服务类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在任何地方工作,而不受限于物理地点。这种新型的工作地点模式对传统的工作地点模式产生了挑战。劳动者也可以自由安排工作时间,不受限于固定的工作时间。
社会上一个倍受赞同的观点是,新生代劳动者的就业观念发生了改变,更偏好灵活的工作时间和地点。尽管该观点缺乏严格的证据,但得到了大量企业管理者的认同。新生代劳动者更愿意选择新就业形态的另一个原因,在《资本论》中可以找到答案:劳动分工对工人就业产生的不利影响是使工人长期从事同一局部的劳动或操作,才能不会得到充分的发挥,技能单一、弱化。这对工人的身心造成很大的损害,而且技能的单一使其在被解雇后很难找到工作。相比较而言,新就业形态的技能要求更加全面,任务完整性更高,劳动者工作更有成就感。在数字经济出现之前,劳动者没有太多就业选择,去制造业企业从事相对单一技能的工作可能是较好的选择。但现在新就业形态可以提供更高的收入水平和更多样的职业体验,劳动者选择“用脚投票”符合市场运行的规律。
此外,对新就业形态带来的劳动者流动问题还可以从新就业形态产生和扩散对国家间贸易影响的角度考虑。首先,劳动者可以跨越国界在线完成工作,即形成所谓的“个人的全球化”,这将导致劳动力流动性增加,从而影响贸易中国家劳动力的需求和供给。其次,新就业形态可能会改变贸易中国家的就业结构,使得一些行业的就业机会减少,而其他行业的就业机会增加。这可能会影响贸易中国家的出口和进口情况。最后,新就业形态可能会改变贸易中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使一些国家的劳动力成本降低,而其他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增加。这可能会影响贸易中国家的竞争力。
第四,新就业形态会改变劳动者的社会保障体系。我国已经逐步构建起灵活就业劳动者的社会保险参保体系,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保障水平偏低和社保参保仍然存在障碍。新就业形态在面临与灵活就业同样问题的基础上,也面临着平台企业、劳动者与劳务承包商之间的责任划分尚不明确问题。当出现劳动争议时,仲裁机构或法院缺乏统一的裁判参照,导致争议解决方式存在较大差异,劳动者面临的不确定性较大。
第五,新就业形态会造成劳动者之间的分化。对于一部分劳动者来说,新就业形态可能带来更多就业机会,包括一些在传统劳动力市场难以获得工作的劳动者。新就业形态中的劳动力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获得收入,如完成多个项目获得收入、为企业提供服务获得报酬、利用网络平台进行商业活动获得收益等。这些会使劳动者的收入变得更加稳定。但对于另一部分劳动者来说,新就业形态可能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的挑战。因为新就业形态使劳动力缺乏传统的社会保障体系,这可能会对一些劳动力的生活水平和工作安全造成影响。此外,新就业形态可能会对一些劳动力的收入水平产生不利影响,因为劳动力的收入来源变得不稳定。新就业形态可能会对不同的劳动者群体产生不同的影响,但具体的影响情况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分析。
新就业形态“扩面”效应减弱
我国的新就业形态发展在世界范围处于前列,在从业者规模、服务覆盖范围和行业渗透率方面处于较为领先的地位。我国新就业形态从“十三五”初期出现,发展到现在规模增长迅速,已经成为当前及未来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十三五”时期经济增速下行但城镇新增就业仍然保持高位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4]。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调研数据显示,2022年深圳市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约160万,已经占到当地就业人员的12.9%。
2020—2022年,社会对食品和各类物资配送的需求增加,由此推动了外卖平台从业者数量大幅增加。另外,由于线下活动受阻,在线平台市场和社区经济、粉丝经济从业者也大幅度增加。但平台经济发展动能减弱,新就业形态向其他服务业类别“扩面效应”减弱。同时,受资本市场波动的影响,以平台商业模式作为创新项目受资本关注度下降。此外,平台企业的顶尖技术人才在向新加坡、硅谷等地区流失。因此,在资本、人才方面,新就业形态的发展受到了影响。
新就业形态发展需要更大的支持力度

图源:VEER
“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是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新就业形态提出的发展要求。如果将新就业形态看成灵活就业的一部分,长期以来我国灵活就业的现实是规模大、保障程度低,不少劳动者被迫进入灵活就业状态,缺乏劳动法律保障体系支持,也无法获得职业技能、收入水平等方面的提升,因此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确实是提升劳动者劳动权益保障水平,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重要保证。
我国政府已经着手不断提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权益保障水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方面,主要通过降低灵活就业门槛为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参保创造条件,重点在“扩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指出,“放宽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条件,实现社会保险法定人群全覆盖”,各地区正着力放宽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条件。身份类别和劳动权益保障内容方面,2021年7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八部门共同印发了《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从国家层面系统地为规范新就业形态提供了政策依据,平台服务类新就业形态最紧迫的职业伤害问题也开始通过职业伤害保险予以解决。2022年7月,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险试点开始实施。
但是,除了灵活就业的视角,也应该看到新就业形态的特殊性和创新性,看到新就业形态对我国劳动力市场发展带来的新动力,对待新就业形态,应从以规范为重点转变为以支持为重点。
(一)就业权是新就业形态劳动权益保障核心要义
劳动权益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在具体的劳动权益中,就业权是所有劳动权益的原权(张成刚,2021),是最应该受到保护和关注的。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权益保障,首先应重视就业权的保障,不能出台可能导致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就业权大面积受损的政策措施。强调就业权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保障其他类别劳动权益可能与就业权之间存在平衡(Trade-off)关系。加强其他劳动权益保障,会增加平台企业运营成本,可能会降低对劳动者的需求。
目前,应特别重视发挥新就业形态的岗位创造功能,不能因为过度保护而使本应创造出的岗位消失。
(二)劳动权益保障争议占比有限
根据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对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劳动权益争议的统计,在劳动争议案件总体中,涉及新就业形态劳动权益争议的比例低于1%,这一数量反映了当前阶段劳动权益保障并非新就业形态发展的主要矛盾,其劳动权益状况要好于传统灵活就业,部分维度甚至好于传统就业。
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完善新就业形态劳动权益保障有利于新就业形态的长远发展。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主要应该明确劳动者与平台企业之间的责任划分,增加双方预期的确定性,这也是新就业形态长期发展的支撑。对于新就业形态劳动权益保障,应仔细分析其劳动权益保障不足点,并逐步完善,对不同类别新就业形态劳动权益保障的突出问题进行分析。目前,比较多的是以线下交易为主的平台服务类新就业形态,应根据行业施策,解决实际中存在的主要矛盾,如外卖骑手可能遭遇交通风险,但互联网营销师在这方面的风险就小很多。应明确派单规则、计费规则、考核规则等,加强对劳动者的宣导,使各项规则公开透明,从而尽可能减少劳动争议问题。
(三)政府与企业需协同治理
目前,大部分政策是从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角度出台的。无论从平台企业发展还是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发展角度,目前对新就业形态的支持政策还是非常有限的。《“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提出了实施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支持保障计划,其中实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技能提升项目已经在部分省份试点实施(张成刚和辛茜莉,2022)。支持新就业形态发展还有大量工作可以开展,需要从中央政府到地方进一步开拓思路,找准机会,通过政策设计为新就业形态发展提供支持。实践证明,以政府与平台企业协同治理的方式会更好地达成政策目标。
应大力支持新就业形态发展,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降低从业者参与新就业形态的准入门槛,保障从业者的公平就业权,完善从业者职业培训、技能认定等职业发展内容,推动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商业保险市场完善等。
注释:
[1] 例如网约车平台是典型的双边市场,而外卖平台属于三边(消费者、骑手、商户)或四边市场(消费者、骑手、商户、服务商)。
[2] 见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课题组《灵工时代:抖音平台促进就业研究报告》,作者认为灵工具有灵活、灵感和灵捷的特征,因此定义为灵工。
[3] 例如,2001 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下发的《关于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无雇工的城镇个体工商户、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可以依照本条例规定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4] 2018 年12 月14 日,国家统计局原人口司司长李希如在解读当年11 月份就业形势中提道:“以网络平台型就业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不断涌现,吸纳了大批就业人员。”
参考文献:
[1] Evans PC and Gawer A. The Rise of the Platform Enterprise: A Global Survey [EB/OL]. (2016.01.14) [2020.08.08]. https://openresearch.surrey.ac.uk/esploro/outputs/report/The-Rise-of-the-Platform-Enterprise/99516671002346.
[2] Joo, Bashir Ahmad, Sana Shawl. COVID-19 Pandemic and the Rising Gig Economy: An Emerging Perspective [J]. Global Economics Science, 2021:16-23.
[3] Kikuchi, Shinnosuke, Sagiri Kitao, et al. Who suffers from the COVID-19 shocks? Labor market heterogeneity and welfare consequences in Japan [J]. 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es, 2021(59): 101117.
[4] 柏宁湘, 郑永新. 寻找新的就业突破口和途径——对上海非正规就业状况的调查 [J]. 工会理论研究, 1997(4): 32-35.
[5] 陈淮. 积极发展非正规就业 [N]. 人民日报, 2000-10-23(009).
[6] 姜奇平. 分享经济:垄断竞争政治经济学 [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7.
[7] 威廉·鲍莫尔. 创新力微观经济理论 [M]. 上海: 格致出版社, 2018.
[8] 晓白. 重视“非正规就业”[N]. 人民日报, 2001-04-09(005).
[9] 欣达. 非正规就业展示广阔前景 [J]. 上海人大月刊, 1997(6): 16-17.
[10] 张成刚. 就业发展的未来趋势,新就业形态的概念及影响分析 [J].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2016(19): 86-91.
[11] 张成刚, 祝慧琳. 中国劳动力市场新型灵活就业的现状与影响 [J]. 中国劳动, 2017(9): 22-30.
[12] 张成刚.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劳动权益保障:内容、现状及策略 [J].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 2021, 35(6): 1-8+120.
[13] 张成刚, 辛茜莉. 让政府、平台、劳动者三方共赢——以公共就业服务融合新就业形态为视角 [J]. 行政管理改革, 2022(2): 79-87.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仅供读者参考,并不作为投资、会计、法律或税务等领域建议。编辑:潘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