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中国居民最终消费不足的问题

导语
增加中国居民最终消费政策选项需要统筹兼顾各类社会经济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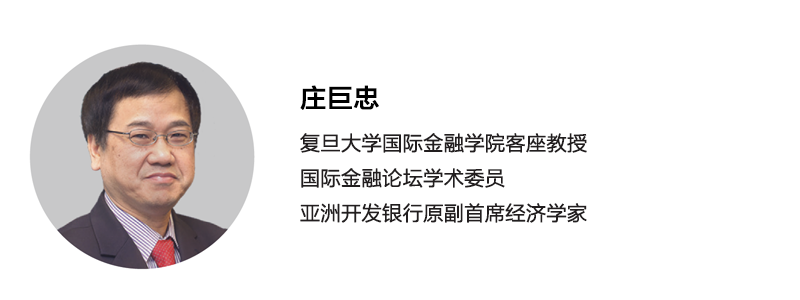
2023年7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内需不足”是当前经济面临的困难挑战之一,强调“要积极扩大内需,发挥消费拉动增长的基础性作用”。2023年12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实施中期评估报告》也指出,总需求不足仍是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特别是最终消费占GDP比重偏低,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不健全。居民消费在一个国家的最终消费中占据主导地位。近年来,不少地方政府通过发放消费券刺激居民消费、支持增长、创造就业。本文通过国别比较(见表1),分析讨论中国居民最终消费的差距和消费不足成因,影响未来几年居民消费和储蓄变化的主要因素,以及扩大居民最终消费的政策选项。
 与他国居民最终消费的差距有多大?
与他国居民最终消费的差距有多大?
众所周知,与大多数高收入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相比,中国居民最终消费支出的 GDP占比偏低。由于居民最终消费中有一部分是由政府和非营利机构直接提供和支付的,因此国家或经济体之间的比较用“居民实际最终消费支出”这一概念更加合适。根据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下简称经合组织)和欧盟委员会联合修订的2008年版《国民收入核算体系》[1],GDP中居民实际最终消费支出由三部分组成:居民最终消费支出、非营利机构向居民提供的实物和服务,以及政府对居民的实物转移支付。后两部分又合称为社会实物转移支付,包括居民享受的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各种免费社会服务以及各类消费性价格补贴(如能源、住房和食品补贴)。非营利机构向居民提供的实物和服务的GDP占比通常很小,所以社会实物转移支付极大部分由政府提供。
表1基于经合组织、亚洲开发银行(亚行)以及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官方数据,包括数据网站和统计年鉴提供的国民收入核算表、居民账户表、投入产出表和资金流量表,估算和比较世界主要经济体2018—2019年居民最终消费支出、社会实物转移支付、居民实际最终消费支出、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居民总储蓄的GDP占比。
表1显示,2018年和2019年,中国居民最终消费支出的GDP占比为38.9%;而美国这一占比为67.5%,比中国高近29个百分点;亚洲除中国以外的5个主要发展中国家(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平均为59.4%(加权平均,下同),比中国高约20个百分点;欧盟27国和东亚3个高收入经济体(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平均各为53%,比中国高14个百分点。
2018—2019年,中国社会实物转移支付的GDP占比为5.8%。而同期美国社会实物转移支付的GDP占比为6.0%,与中国相仿;欧盟27国和日本分别为12.9%和12.1%,均约为中国的两倍;韩国为9.2%,也高于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分别为3.2%和3.4%,低于中国。
亚洲其他经济体这一数据缺损,但如果用公共最终消费支出中教育、医疗卫生和其他社会服务支出的GDP占比作为一个近似值,泰国为8.0%,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不到6%,中国台湾地区约为6.5%。
综上所述,与欧盟、日本和韩国相比,中国居民实际最终消费不足表现在偏低的居民最终消费和社会实物转移支付的GDP占比两个方面,分别能够解释全部差距的70%和30%。与美国和亚洲5个主要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居民实际最终消费不足完全是由于偏低的居民最终消费的GDP占比。
根据经合组织和亚洲开发银行汇编的投入产出表数据,与高收入国家和经济体相比,中国居民最终消费支出的GDP占比偏低似乎主要体现在服务消费的不足。以2018—2019年为例,中国服务消费占居民最终消费总支出的67%,相当于GDP的26.1%。而美国这一比例超过80%,相当于GDP的55%;欧盟27国和东亚3个高收入经济体平均分别为72%和75%,相当于各自GDP的38.6%和39%;亚洲5个主要发展中国家平均为54.3%,相当于GDP的33%。尽管亚洲5个主要发展中国家的服务消费在居民最终消费总支出的占比低于中国,但由于其最终消费总支出的GDP占比远远高于中国,其服务消费的GDP占比也高于中国。中国居民最终商品消费的GDP占比与美国、欧盟、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和泰国接近,但也远远低于其他国家和经济体。
但是在比较这些数字时,我们应该非常谨慎。有两个原因可能导致中国居民最终服务消费的GDP占比被低估:第一,中国国民收入核算中用于估算自住房屋虚拟租金的方法与大多数高收入国家使用的方法不同。中国采用历史成本直线折旧法估算虚拟租金,而大多数高收入国家根据市场租金来估算。因此,在大多数高收入国家,虚拟租金通常占GDP的5%~10%。在美国,虚拟租金的GDP占比在7.5%左右。而在中国,据估算,虚拟租金只占GDP的2.5%[2]。根据经合组织和亚洲开发银行汇编的投入产出表数据,2019年中国居民房地产最终消费支出(包括自住房屋虚拟租金)的GDP占比为4.5%,日本为14%,美国为10.7%,欧盟平均为8%,印度为6.8%,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平均为6.5%。
各国之间同一商品或服务的价格差异也会导致各商品或服务GDP占比的差异。众所周知,由于税收、价格补贴、不同的工资水平、市场竞争状况、汇率波动等多种原因,同一商品或服务在不同国家的价格用市场汇率换算成同一货币时通常不一样,使不同国家之间收入和消费水平不可比。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用购买力平价将不同货币兑换成一种共同货币,并在兑换过程中控制经济体之间价格水平的差异使不同货币的购买力相等。根据世界银行国际比较项目的结果[3],2017年中国几类主要的服务包括医疗卫生、教育、住房、公用事业和交通相对于美元的购买力平价均低于3(人民币元/美元),而GDP的平均购买力平价为4.2(人民币元/美元),同年市场汇率全年平均大约为6.76(人民币元/美元)。也就是说,用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居民服务消费的GDP占比与美国的差距可能没有如前所述的那么大。
是居民收入太低,还是储蓄太高?

图源:VEER
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取决于两个变量,一个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另一个是居民储蓄。2018—2019年,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包括资本折旧,下同)占GDP的59.7%。
同期美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GDP占比为78.3%,比中国高出近19个百分点;欧盟27国和东亚3个高收入经济体平均各为60%,与中国相仿;亚洲5国主要发展中国家平均为73.4%,比中国高约13个百分点,其中印度和菲律宾分别为80%和78.4%,远高于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三国平均为61%,跟中国接近。2018—2019年,中国居民总储蓄(包括资本折旧,下同)占GDP的20.8%。同期美国居民总储蓄的 GDP占比为10.8%,比中国低10个百分点;欧盟27国为7.3%,比中国低13.5个百分点;东亚3个高收入经济体平均为7.1%,比中国低13.7个百分点;亚洲5个主要发展中国家平均为14.1%,比中国低6.7个百分点——其中印度为19.9%,与中国相仿;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4国平均为5.7%,比中国低15个百分点。
上述数据表明,中国居民最终消费支出GDP占比与美国的差距2/3是由于中国偏低的居民可支配收入,1/3是由于中国偏高的居民总储蓄;与印度的差距极大部分是由于中国偏低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但是与欧盟27国、东亚3个高收入经济体和除印度和菲律宾外的亚洲几个主要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几乎全部是由于中国偏高的居民总储蓄。
中国居民总储蓄的GDP占比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6%~7%上升到1992年的23%,然后下降至21世纪初的17%左右。之后又一路上升到2012年的22%,然后一直在20%~21%波动。由于新冠疫情限制了居民消费,2020年这一占比增加到了23.5%。近年来,对中国居民储蓄行为的研究发现,多重因素导致了居民储蓄率的快速上升:第一是人口结构的变化,包括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上升和独生子女政策所带来的家庭规模的缩小。与老年人相比,劳动年龄人口储蓄更多,而家庭规模的缩小使劳动年龄人口能够储蓄更多。
第二是住房制度的改革,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因为居民购房支出属于储蓄,城市统配房向商品房制度的转变通过首付效应和抵押贷款支付效应提高居民储蓄率,而房价的快速上涨(2000—2022年全国住宅商品房每平方米平均销售价格年均增长8.4%)使这些效应进一步被放大,尽管私有住房的财富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会抵消这种影响。
第三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变迁。主要是因为在城市,计划体制下的“铁饭碗”被打破,养老和医疗福利被大幅削减,在农村,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制度被取消,但进行这些改革的同时并没有及时建立足够的社会安全网,导致居民增加预防性储蓄。
第四是收入差距的扩大。原因是低收入家庭储蓄率低,而富裕家庭储蓄率高。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不到0.3上升到2008年的0.491,尽管2008年之后有所下降,基尼系数仍处于高位。[4]
第五是经济增长的加速。这可能是由于消费行为的惯性,使居民的消费增长滞后于收入增长,也可能是因为消费者根据长期预期收入而非当前收入进行消费决策,这两种可能都会导致居民储蓄率的上升。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项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中国居民储蓄率的全部增量中,约有一半是由人口结构变化所引起的,住房制度改革贡献了25%,社会保障制度的变迁贡献了约17%,收入差距的扩大贡献了余下的8%。[5]根据笔者的估算,2000—2021年,中国居民将总储蓄的35%~40%用于购置新建住宅商品房,占全国新建住宅商品房销售总额的70%左右(其余30%利用房贷购置)。也就是说,过去二十几年居民总储蓄GDP占比增加了4~5个百分点,主要由购房需求所驱动。
展望中国居民总储蓄率的变化

图源:VEER
展望未来,以下因素将有助于中国居民总储蓄 GDP占比的下降:
第一,人口结构的变化,包括人口老龄化和家庭规模的扩大。2021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了总人口的18.9%,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了14.2%。[6]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的测算,预计“十四五”时期,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将超过20%,2035年左右将超过30%。[7]如前所述,老年人口的储蓄率低于劳动人口。另外,2021年5月31日“三孩”政策的出台预计将会有助于提高妇女生育率,从而增加家庭人口规模,降低居民储蓄率。
第二,由于过去二十几年中国经历了城镇私有住房保有量和房价的大幅增长,居民购房的刚需大概率会回落,即使不回落,其增长率也会下降。据估计,2018年全国城镇住房自有率达到了70%,在全球名列前茅;城镇住房套户比达到了1.09,超过部分发达国家。[8]2020年全国人均居住建筑面积达到41.76平方米,其中城市人均居住建筑面积为36.52平方米,达到部分发达国家的水平。[9]购房刚需的回落或其增长的下降将会使住房制度改革作为过去居民总储蓄率增加驱动因素的重要性下降,而私有房产的财富效应也有利于增加消费。
第三,随着中国收入水平的持续上升,包括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在内的公共社会支出预计将不断增加,社保制度将进一步完善,这将有助于降低居民的预防性储蓄。
第四,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会增加对服务业的需求,提高居民消费倾向。
第五,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特别是消费信贷和房贷市场的成熟和年青一代消费行为的变化会导致居民储蓄率下降。
但是,下述因素可能不利于中国居民总储蓄率的下降:
第一,人口结构的变化将带来居民消费行为多大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何时发生还有待观察。有的观点认为,由于预期寿命的不断提高,老年人在老年生活的早期阶段可能会继续工作和储蓄,所以不能排除老龄化带来所谓的“银色红利”的可能。同时,自2016年中国政府开始放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每年新生儿数量并未显著增加,因此,“三孩”政策对鼓励年轻夫妇生育更多孩子的效果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第二,经过几十年的改革,社会保障已实现近乎全民覆盖,但城镇和农村居民之间、城镇职工和农民工的养老和医疗保险差距仍然很大。根据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nese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CHIP) 数据,2018年农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人均养老金收入只有城镇的10%左右,而农民和城镇职工的差距更大,可能高达20几倍。[10] 社会保障的不足会导致居民继续增加预防性储蓄。
第三,尽管居民购房的刚需会回落或其增长会下降,但综合考虑城镇化进程、居民收入增长、改善性住房需求等因素,中国房地产市场仍有较大发展空间,可能逐步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所以房需仍将是居民储蓄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
第四,尽管中国整体上用基尼系数衡量的收入差距近年有所缩小,但仍处于较高水平,而且收入差距缩小的主要原因是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而城镇内和农村内的收入差距不见明显下降。[11]
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在过去半个世纪都经历了居民储蓄率快速上升然后下降的过程。日本居民总储蓄的GDP占比估计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15%左右增加到了70年代中期的27%,然后开始下降,到21世纪初下降至10%左右,2010—2019年平均大约为6%。[12]韩国居民总储蓄的GDP占比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不到10%上升至80年代末的25%,然后开始下降,到90年代末下降至10%左右,2010—2019年平均为6%多一点。[13]中国台湾地区居民总储蓄的GDP占比从20世纪50年代中的不到5%左右上升至90年代初的18%,然后开始下降,2010—2019年平均为10%左右。[14]这些经济体都经历了妇女生育率、劳动人口比例和经济增长率快速上升然后下降;人均收入、平均寿命和老年人口比例逐步增加;中等收入阶层规模扩大;房地产投资热和房价飙升;社会安全网不断完善和金融业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日本居民总储蓄的GDP占比从其高峰降至10%大概用了25年时间,韩国用了十几年时间,中国台湾地区大约用了20年的时间。
综上所述,未来几年或几十年中国居民最终消费和总储蓄GDP占比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人口结构、城镇化进程和房需、社保制度、收入分配、经济增长速度和发展水平的变化。从中长期来看,居民最终消费的GDP占比将会逐步上升,居民总储蓄的GDP占比将会逐步下降,但上升和下降的速度和幅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房需将继续是居民储蓄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
增加居民最终消费的政策选项

图源:VEER
长期偏低的居民最终消费支出的GDP占比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经济结构和发展的不平衡,会影响增长的可持续性和发展的质量,需要政策干预。特别是在目前外需疲软、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需求回落的情况下,增加居民最终消费的GDP占比显得尤为重要。
根据笔者的分析,尽管没有捷径可走,增加居民最终消费支出的政策应该着眼于三个方面:①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②鼓励居民减少储蓄,增加最终消费,特别是增加服务消费;③继续推进供给侧改革,特别是要发展服务业,同时加速产业升级。
第一,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改善收入分配,扩大中产阶层的规模。如前所述,全国平均而言,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GDP占比与除美国、印度和菲律宾外的其他国家或经济体接近,所以重点是要增加低收入群体特别是农村人口的可支配收入。措施包括:①继续推进城市化,创造更多的城市就业,促进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同时改革户籍制度,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②通过加强对农业的投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发展规模经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来增加农民收入;③完善最低工资制度,确保最低工资能够真正起到保障劳动者个人及其家庭成员基本生活的作用;④完善税收制度,使税收在收入再分配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二,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基本公共服务,减少居民预防性储蓄的需要。特别是要加强农村的社保系统和农民工的社保待遇,包括农村人口和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和各类基本社会服务,缩小城镇和农村之间、城镇职工和农民工之间社保的差别。同时可以适当增加社会实物转移支付,特别是通过增加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的公共支出,适当提高政府实物转移支付的 GDP占比,并进一步推动教育、医疗和其他社会服务机会的均等化。
第三,通过增加保障性住房的供给,减少房需驱动的居民储蓄。保障性住房可以包括公租房、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以满足不同收入水平、不同阶层居民的住房需求。同时要规范住房租赁市场,更好地保护租客和房主双方的利益。尽管目前全国平均房价呈回落趋势,不能排除将来继续上涨的可能。稳定房价,使房价水平与居民收入水平相匹配,对减少房需驱动的居民储蓄至关重要。
第四,推行一些有效的针对“三孩”政策配套措施,提高妇女生育率。提高妇女生育率既可以改善人口结构,解决中国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也可以增加居民最终消费支出。措施可以包括扩大妇幼健康服务供给,提升普惠性学前儿童教育的覆盖率,增加义务教育年限,减轻家庭教育负担,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等。
第五,推动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利用财富效应提高居民消费倾向。过去十多年中国上市公司数量和股市市值大幅增加,但股价停滞不前。提振市场信心、繁荣股市能够提高居民收入预期,增加财富效应,从而增加消费。推动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需要加强上市公司的治理,完善信息披露制度,鼓励上市公司分红,扩大机构投资者的参与,加强市场监管和投资者保护。
第六,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对增加居民最终消费必不可少。特别是要更加注重发展服务业,包括教育、医疗卫生、文体、休闲和旅游,继续推进服务业市场导向的改革和开放,加速服务业的数字化转型;同时要鼓励创新,加强产业升级,使企业能向居民不断提供更多更新和更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创造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
第七,国家统计局也要不断健全国民收入核算体系,加快与国际接轨,提高统计数据的质量,使统计数据与其他国家更加可比,从而使政策措施更加精准。增加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减少对投资的依赖,将使中国的经济增长更加健康、稳定和可持续,也可以使当代和后代中国百姓的生活水准和福祉更加平衡。
[1] 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 Division. The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EB/OL]. (2024.1.25) [2024.1.25]. https://unstats.un.org/unsd/nationalaccount/sna.asp.[2] 王瑞民, 王微. 国研中心|估“实”居民自用住房虚拟租金的时机已经成熟[EB/OL]. (2022.7.27) [2024.1.22].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9194788.[3] World Bank.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EB/OL]. (2021.3.31) [2024.2.19]. https://databank.worldbank.org/embed/ICP-2017-Cycle/id/4add74e?inf=n. [4] Zhuang J, Zhan P, Li S. Accounting for changes in income inequality in China, 2002–2018: evidence from household survey data[J]. Asian‐Pacific Economic Literature, 2023, 37(2): 3-26.[5] Zhang M L, Brooks M R, Ding D, et al. China’s high savings: drivers, prospects, and policies[M].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18.[6] 国家统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 (2022.2.28) [2024.1.25]. https://www.stats.gov.cn/xxgk/sjfb/zxfb2020/202202/t20220228_1827971.html. [7] 人民网. 我国预计2035年左右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 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EB/OL]. (2022.9.20) [2024.1.23]. http://health.people.com.cn/n1/2022/0920/c14739-32530182.html.[8] 任泽平. 中国住房存量报告:2021[EB/OL]. (2021.6.24) [2024.2.5]. https://www.yicai.com/news/101090058.html.[9] 每日经济新闻. 最新数据:中国人均住房面积超41平方米,平均每户居住面积达111平方米[EB/OL]. (2022.6.27) [2024.2.5]. https://new.qq.com/rain/a/20220627A04FN400.[10] 贾晗睿, 詹鹏, 李实. “多轨制”养老金体系的收入差距——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的发现[J]. 财政研究, 2021(03): 101-114.[11] Zhuang J, Zhan P, Li S. Accounting for changes in income inequality in China, 2002–2018: evidence from household survey data[J]. Asian‐Pacific Economic Literature, 2023, 37(2): 3-26.[12] Jun SAITO. Household Savings Rate in Japan [EB/OL]. (2024.1.17) [2022.1.25]. https://www.jcer.or.jp/english/household-savings-rate-in-japan. [13] Horioka C Y, Terada-Hagiwara A. The impact of sex ratios before marriage on household saving in two Asian countries: The competitive saving motive revisited[J]. Review of Economics of the Household, 2017, 15: 739-757.[14] Athukorala P C, Tsai P L. Determinants of household saving in Taiwan: Growth, demography and public policy[J].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003, 39(5): 65-88.
[1]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Household disposable income [EB/OL]. (2024.1.22) [2024.1.22]. https://data.oecd.org/hha/household-disposable-income.htm.[2]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Household accounts [EB/OL]. (2024.1.22) [2024.1.22]. https://data.oecd.org/economy.htm#profile-Household%20accounts. [3]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put-Output Tables (IOTs) 2021 ed [EB/OL]. (2024.1.22) [2024.1.22]. https://stats.oecd.org/Index.aspx?DataSetCode=IOTS_2021. [4]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Stat. Annual national accounts – detailed non-financial accounts - non-financial accounts by sectors. [EB/OL]. (2024.1.22) [2024.1.22]. https://stats.oecd.org. [5] Asian Development Bank. Data and Statistics [EB/OL]. (2024.1.22) [2024.1.22]. https://www.adb.org/what-we-do/data/regional-input-output-tables. [6] 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2020 [EB/OL]. (2020.9.20) [2024.1.22]. https://www.stats.gov.cn/sj/ndsj/2020/indexch.htm. [7] 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2021 [EB/OL]. (2021.9.20) [2024.1.22]. https://www.stats.gov.cn/sj/ndsj/2021/indexch.htm. [8] BPS-STATISTICS INDONESIA. Indonesia Household Accounts 2019-2021 [EB/OL]. (2022.10.31) [2024.1.22]. https://www.bps.go.id/en/publication/2022/10/31/ad989944404ff435bf53dd46/indonesia-household-accounts-2019-2021.html. [9] BANGKO SENTRAL NG PILIPINAS. Philippine Flow of Funds 2020[EB/OL]. (2024.1.22) [2024.1.22]. https://www.bsp.gov.ph/Media_And_Research/Philippine%20Flow%20of%20Funds/FOFReport2020.pdf.[10] BANGKO SENTRAL NG PILIPINAS. Philippine Flow of Funds 2019 [EB/OL]. (2024.1.22) [2024.1.22]. https://www.bsp.gov.ph/Media_And_Research/Philippine%20Flow%20of%20Funds/FOFReport2019.pdf.[11] Government of India. Indian Budget. Economic Survey 2022-23 Statistical Appendix[EB/OL]. (2024.1.22) [2024.1.22]. https://www.indiabudget.gov.in/economicsurvey/doc/Statistical-Appendix-in-English.pdf.[12] Thailand Office of The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Council. National Account[EB/OL]. (2024.1.22) [2024.1.22]. https://www.nesdc.go.th/nesdb_en/main.php?filename=national_account. [13] 中华民国统计资讯网. 调查报告[EB/OL]. (2024.1.22) [2024.1.22]. https://www.stat.gov.tw/News_Content.aspx?n=3908&s=231908. [14] Bank of Korea. ECOS Economic Statistics System. National Account[EB/OL]. (2024.1.22) [2024.1.22]. https://ecos.bok.or.kr/#/.
[15] The Star Business. Malaysia's 2021 gross national savings grew 19.1% to RM402.6bil - DoSM[EB/OL]. (2023.12.19)[2024.1.25]. https://www.thestar.com.my/business/business-news/2023/12/19/malaysia039s-2021-gross-national-savings-grew-191-to-rm4026bil---dosm.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仅供读者参考,并不作为投资、会计、法律或税务等领域建议。编辑:潘琦。